关于衰老与老年生活质量,以及《最好的告别》
A Thought-Provoking Exploration of Aging and End-of-Life Care and A Review of Being Mortal by Atul Gawande
你得做好“那样”的准备,我父亲的医生把我单独从病房里叫出来,对我这样说。
在2022年5月,我的父亲因中风住院,我回到他的城市照顾了他四个月,这是这十几年来我呆在老家最久的一次。父亲的出院诊断的项目有十多条,多发性脑梗死和左侧偏瘫是这次住院主要原因,另外也做了颈动脉支架,希望藉此疏通狭窄的颈动脉防止之后再度中风,除此之外还有高血压3级(极高危)、动脉粥样硬化、II型糖尿病、高尿酸血症、卒中后抑郁、睡眠障碍等慢性症状。
我的父亲当时70岁,这是他的第三次中风,这次中风彻底让他失去了自理能力。他只有我一个孩子,而我的母亲也在卒中后康复治疗没法照料他。所以,在父亲住院的这段时间,是我和我父亲的80岁的姐姐(也就是我姑妈)在照料他,作为家属,我们也感到非常疲惫。
父亲的病情非常反复,也遭遇了许多我们未曾想到的并发症,几度进出NCU(卒中重症病房)和ICU。
不那么严重的情况是,他在手术后发生了尿路感染,低烧了四五天,只能卧床修养,耽搁了康复运动;而比较严重的情况是,由于在卒中后需使用双抗药物治疗(抗血小板+抗凝血,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),而长期卧床不能活动也又重了他便秘的症状,坚硬的粪块和被抑制的凝血功能,导致他数次肠道大出血。其中有一次非常危急,由于肠道出血,送进ICU之前他的血压已经掉到了76/48,在那之后的24小时内我签了四份病危通知书。医生曾把我带到一边,小声对我说,要做好“那样”的准备。
“那样”的准备,在肾上腺素随时要爆发的当下,我自然知道是怎样的情形,我克制着自己的情绪,和多个科室的医生商量对策,尽量理智考虑着那时应该怎么办。回头再看,继续“战斗”还是“放手”,这个决定并不是我做出来的,而是医护人员们帮我做了选择——尽量延续宝贵的生命。而我也无法做到真正的理智,我并不知道父亲所求的是什么,也不知道他能放弃什么,之后要如何生活,或者说生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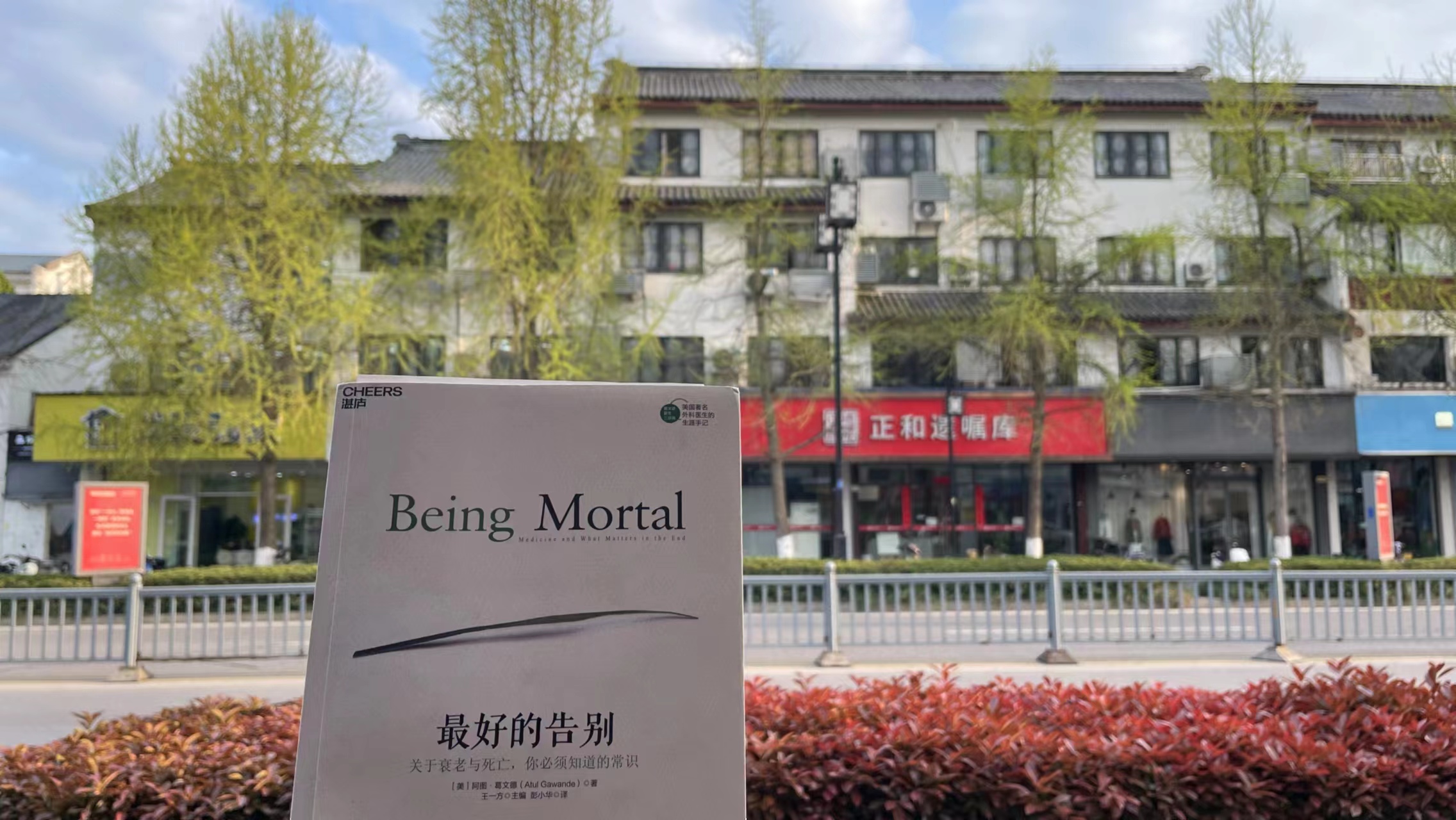
在那时,我知道了一本书,名为《最好的告别》,英文原名为 Being Mortal。这本书于2014年出版,作者阿图·葛文德(Atul Gawande)是一名外科医生,他在书中探讨了人们在衰老时,在接近生命终点时,所面临的挑战和选择。葛文德提及了他作为外科医生时接触到的真实病例,以及他照顾自己父亲的经验,认为现代医学在处理生命末期问题上存在局限性,并对我们如何改善对接近生命终点的人的护理提出了见解——以病人为中心。
或多或少,我是希望能从这本书里找到答案,找到一些应对之策,能够让我在“那样”的情形最终到来时,我有着足够的思想武器,去冷静应对我所需要去面对的事情。
有那么一些事情,我已经在应对,就是我父亲出院之后的养老和生活。
在家,彼此折磨
出院后,我父亲几乎没有了自理能力,他的左手、左腿无法行动,不能自行走路,所以无法自己去上厕所,无法从躺着的姿势自己坐起来,无法自己洗澡;唯一尚可的活动是翻身和进食,他的右手还可以活动,把碗饭放在他面前,他可以自己用勺子将饭菜放入口中,通常会让食物撒上一身,因此跟他佩戴了一个围兜,他并不满意,可是没有办法。
我们请了住家保姆保姆照料我父亲,计划是我和保姆先一起照料一段时间,等保姆熟悉之后,我再回到我工作的城市。
我们请的保姆非常专业,曾经在养老院工作。他做事认真负责,他很快适应了环境,对我父亲的口服药和胰岛素注射,有准确的时间记录,此外,他做饭做菜也很在行。
可事实上,我们发现这行不通。我父亲总是在凌晨两点醒来,叫喊着要小便,可是当我把尿壶放到正确位置,等他解小便,五分钟,十分钟,二十分钟过去了,他依然尿不出来。于是便想着作罢,我拖着困倦的身躯回床上休息。可不到五分钟,他又喊着要小便,但是依然解不出来,在晚上循环着这样的操作。
有时候他会喊着要开风扇,有时候在凌晨四点钟,他会喊着要刷牙,也会喊着要安眠药,大多是时候他会叫我的名字,他也会叫着保姆的名字,偶尔他也会叫着之前住院时照顾他的护工的名字——仿佛父亲不知道他出院了,不知道白天和黑夜,不知道他已经服用了安眠药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和保姆在夜间无法休息,而白天又需要持续照顾我父亲。有时候,我们选择在半夜里不理我父亲,结果他会拿起手机给姑妈打电话,姑妈因此高血压发作了。
仅仅几天,我们就来到崩溃的边缘,而给我们最终一击的是他的排便问题。在三天没有排便后,我们要对他进行人工干预——如果大便秘结而用力排便,容易诱发卒中——我们向他的肛门中注入开塞露,然后打算用手抠出干硬的大便。这个过程非常不顺利,后来演化成了一场灾难。
这是一段短暂的共同居住时间,对居家照料进行了尝试。我面对着越来越无法持续的情况,不得不做出选择,一面是我逐渐失去控制的生活和工作,一面是越来越脆弱、依赖性极高的我的亲爱的父亲。
在《最后的告别》中,我读到了几乎相似的场景,路和他的女儿谢莉的故事。88岁的路和女儿谢莉共同生活,而谢莉也需要照顾她自己正在上高中的孩子们,她的丈夫失业了一年半。谢莉的工作不只是路的护理员,而是“全天候看门人兼司机兼日程经理兼医药和技术难题解决者,同时还是厨师兼侍女兼服务员,更不用说是挣钱养家的人”。
谢莉觉得自己的神志在弱化,她想当个好女儿,她希望父亲安全,也希望他快乐,但她也想要一份可以控制的生活。有一天晚上,她问丈夫是不是该给老人找个地方。仅仅因为有这个想法她就觉得很羞愧,这违背了她对父亲的承诺。
被困在养老院
我们不得不把父亲送到养老院去照料,那里的护工有更丰富的经验应对这些情况(比如便秘患者的排便问题)。我和姑妈,还有保姆所在家政公司的负责人在楼梯间里一起商量这件事,我们想象不到什么更好的选择。
按照中国的城市等级划分,父亲所在的城市城区常住人口94万,已经非常接近Ⅱ型大城市了,在养老的供需方面按理说应该存在比较充足的资源,可我们在寻找合适的养老机构方面并不顺利。
我们看的第一家养老院是家政公司推荐的,老板亲自开车带我们去参观那家养老院,环境比较糟糕,阴暗的走廊、狭小的房间、腐败的气味、露天的厨房,老人们被困在床上,他们有的还戴着防抓手套,一副了无生气的样子——这让人觉得这里是动物园,只有笼子和锁链。
我们也尝试去寻找公立养老院,可是这边的公立机构只收纳孤老孤儿,也就是说只有无人赡养的老人,他们才会接受。
在一家公立养老院旁边,我们发现了一家算是不错的养老院。它在一栋有11层的建筑里,其中的2-5楼是一家一级医院,有老年病专科和康复室,6-11楼是养老院,“医养结合”是他的卖点之一。养老院的护工提供日夜的照料,而如果有医疗需求,楼下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可以直接去给与医疗帮助。养老院的环境也算不错,至少是窗明几净、整洁明亮的。我们一边犹疑,一边做出“这是这里”的决定。
可是如何告知我的父亲——他才刚离开医院,回到自己的家不久——需要去养老院这件事。后来,养老院的负责人来充当了“坏人”,她亲自上门检查了我父亲的情况,和他进行了一场谈话。我的父亲并没有反对,他接受了这个安排。
负责人评估了我父亲的护理等级,是护理程度最高的那一级,而后给我父亲做了新冠检测,告诉我们养老院第二天会派车来接我们。
我和父亲居住在一起的最后一个晚上,也是他回家后最安静的一个夜晚,他几乎没有再吵闹。我甚至有一种想法,他是不是在通过行动表示自己晚上也可以很安静(事实上他没有睡着),不打扰大家的睡眠,这样就不必去养老院了。
第二天早上,养老院派了一辆救护车来接他,然而下楼也成了难题,我父亲住在四楼,老房子没有电梯,我们只得用一张毯子兜着我父亲,四个人各拽住毯子的一个角,把他抬到了楼下的担架上,他就这样离开了他居住了二十多年了家。之后便是繁复的文件签署和遗嘱,以及防水垫和一些生活用品的采买,此后,我终于得到了片刻的安宁。
我似乎从照顾父亲的困境中暂时解脱了,可是我父亲并没有。我一直无法准确描述我父亲在养老院的经历,我只是发现他的眼神越来越呆滞,直到我看到了《最好的告别》中对作者妻子的祖母爱丽丝的境况的描述:
他们告诉她,希望通过理疗,她能够重新学会走路并回到她的屋子。但是她再也没有恢复行走能力。从那以后,她只能坐轮椅,受制于刻板的疗养生活。
她丧失了所有的隐私和控制力。大多数时候她穿着病号服。他们叫醒她她就起床,安排她洗澡她就洗澡,让她穿衣服她就穿衣服,叫她吃饭她就吃饭。她和院方安排的人住在一起。她有过好几个同屋,但是她们入住的时候院方都没有征求过她的意见。这些人都有认知障碍,有的很安静,也有的很闹腾,有一个人甚至吵得她整晚睡不着觉。她觉得像个犯人,仅仅因为老了就被投进了监狱。
这和我父亲的状态如出一辙,我们(我、我母亲和我姑妈)都认为,通过康复训练,我父亲是可以恢复一定的行走能力的。因为在他住院期间,卒中的情况稳定之后,发生肠道出血之前,他已经可以扶着扶手从床边走到卫生间了。而他自己偷懒不按规程完成康复项目——二十分钟的蹬车项目只做三分钟就想停下——是他最终没有恢复行走能力的原因。我们似乎都将这一问题的原因归结到他自己身上。
养老院这种“监狱式”的生活方式,是因为出于善意的保护大大压制了对自立和尊严的维护。这不是我父亲一个人的情况,其他自理程度类似的老人也有着相同的境遇。这也不是中国的问题,在美国,在印度,当医疗发展到一定程度,大家也会遇到这个问题——人们不太会突然死亡,而是在衰老脆弱、失去自理能力的情况下,缓慢地走向生命的终点,这一段旅途该怎么进行,是整个社会都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何时放手
在入住养老院三个月后,我父亲的各项生理指标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血糖逐渐恢复到合理的范围,血压也控制在他这个年纪安全的数值之内,可他并不快乐。
他也许是交到了一两个新的朋友,他会和康复医师一起下象棋,但更多时候他只能躺着,或者坐在轮椅上。他在养老院唯一的消遣就是喝水和牛奶,所以他频繁的按铃呼叫护工给他倒水,在护工没来得及响应的时候——他会给我或者姑妈打电话,不分白天和黑夜。
到底是怎样的路径,让我们一步步走到如今的局面。我甚至怀疑给父亲做颈动脉支架手术的正确性,这是否是必不可少的治疗?
我想,我们缺少的是《最好的告别》里提到的“艰难的谈话”——关于我父亲的期望。
我至今不太明白,我父亲对死的态度。在医院里的许多时间里,他都说着“让我死了吧”、“我要安乐死”之类的话,可是真在发生肠道大出血,血液和粪块时不时从肛门涌出,出现休克症状的那一刻,他却说“如果是这样死了,那就太窝囊了”。
在我的父亲被推进ICU,医生告诉我要做好“那样”的准备时,我心理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——让他活下去,只要我的经济还可以承受。
可这并不正确。我并不了解我父亲对“生”和“死”的需求。
在《最好的告别》中,我读到了“临终愿望”这个概念,在生命的那个时刻之前,我们需要回答这4个问题:
如果你的心脏停搏,你希望做心脏复苏吗?
你愿意采取如插管和机械通气这样的积极治疗吗?
你愿意使用抗生素吗?
如果不能自行进食,你愿意采取鼻饲或者静脉营养吗?
当然,比起这些问题,讨论本身更加重要。
我并不太清楚我父亲的愿望,我们曾经谈过遗体捐赠,也谈过骨灰的处理。但对于“如何死”,或者“如何好好活到死”,我只有一个肤浅的概念,就是他希望临终时不要身上插满了管子。我知道这一点,可我并无法将这个愿望传递给ICU的医生。
书中提到一位姑息治疗专家苏珊·布洛克(Susan Block),在她的父亲杰克70岁时是否需要做一个手术切除颈部脊髓包块的时候,他们做了一场谈话:
她告诉他:“我需要了解,为了博取一个活命的机会,你愿意承受多少,以及你可以忍受的生存水平。”谈话进行得非常痛苦。他说:“如果我能够吃巧克力冰激凌、看电视足球转播,那我就愿意活着。如果能有这样的机会,我愿意吃很多苦。”听到这句话时,布洛克完全震惊了……
结果证明这个谈话至关重要,因为手术后,他的脊髓发生出血。外科医生告诉她,为了挽救他的生命,他们必须再做一次手术。但是,出血已经让他近于瘫痪,他会严重残废好多个月,而且很可能永远残废。她希望怎么办?
“我有三分钟的时间做决定。我意识到,其实他已经做了决定。”她问医生,如果她父亲活下来,是否还能吃巧克力冰激凌、看电视足球比赛。可以,他们说。于是,她同意让他们再给他做一次手术。
对我来说,发生的事情,已经无法改变。虽然我实在一切发生后才阅读了《最好的告别》,但他至少给我提了醒,我还可以为将来做好准备:
我也应该和父亲进行一场谈话,了解他对于生和死的期待,在“那样”的情况再次发生之前。
关于我自己,我可能不如我父亲幸运,他至少还有我这个孩子照料他,而我不打算要小孩,我的人生该如何,是我需要探索的道路。